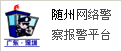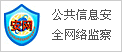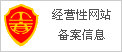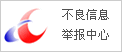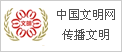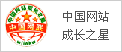異鄉創業者:另一股創新力量的榮與痛
“在原有文化傳統很強的地方往往是一種束縛,移民在進入到一個陌生社會后,原有的傳統在新環境下找不到根基,他們失去了原有的框框,創造力更能被激發出來。”
對于創業者來說,世界越來越像是平的了。
“移民甚至難民往往被視作是消極的現象,我們的職責就是扭轉人們的思維定勢。他們其實像鳥兒一樣,對世界進行探索,找到更好的去處。”去年,Mirela Sula離開了自己的祖國,來到英國倫敦。她曾是阿爾巴尼亞最大的雜志管理人之一,今年她在英國完成了心理學博士學位,創辦了《移民婦女》和《全球女性》這兩本雜志,幫助難民女性創業。
“邊緣人”的創新力
來自巴西的Rafeal Dos Santos在21歲的時候開始學英語。如今,他在倫敦有了自己的企業,幫助難民成為企業家,還由于為難民社區所做的貢獻獲得了英國政府頒發的企業家獎項。
這些移民甚至難民的創業故事只是全球人口流動大潮中的滄海一粟。
“移民創業的比例越來越高,我們五分之一的技術創新公司是由移民創立的。”聊起創業,Mirela熱情滿滿,她甚至引用了喬布斯這一敘利亞移民的例子。“過去一年中,全英國的企業中,有14%是由移民創建。而在美國,這一數字是40%。”
移民作為“邊緣人”的創新能力不容小覷。“在原有文化傳統很強的地方往往是一種束縛,移民在進入到一個陌生社會后,原有的傳統在新環境下找不到根基,他們失去了原有的框框,創造力更能被激發出來。”一名長期研究浙商的學者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舉了幾個例子:前幾年,一些浙商去非洲做紡織生意,和當地酋長關系很好,他們發現那里的自然資源很豐富,且正是國內非常需要的礦種,拿到了幾萬平方公里的采礦權。還有一批此前在非洲做工程建設的國企工人,發現非洲當地土地肥沃,很適合種蔬菜,當地需求也很旺盛,就全家移民過去種菜,獲得非常高的回報。
也有不少老外選擇來中國創業。
“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父母就帶上我成天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那時候我就意識到,中國在幾十年后一定會發生巨變,我應該到中國來見證這一改變。”來自加拿大的Mark Maclntyre在2008年來到中國,從事的第一份職業是醫療記者,如今他運作著一個專供醫療界人士獲取專業資料的微信平臺。
“中國現在正處于這樣的一個階段:每一個經濟體在一開始發展的時候,都會從模仿起步,后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創新,中國現在就有層出不同的新創意和新公司出現。”同樣看好中國創業前景的還有來自荷蘭的Philippe Teunissen,此前他在俄羅斯的創業項目失敗,四年前他來到中國,目前在運作一個企業創新管理的云平臺軟件項目。
還有創業者看到了在中國上海圍繞跨國企業人才的巨大創業機會。來自北歐的Rina Joosten-Rabou告訴本報記者,他們提供的是一個基于數據的人工智能服務,在人才市場可以得到深度應用。
異鄉者的痛
從洗盤子開始,華人在歐洲的移民開起了餐館、超市,做起了貿易,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受過更好教育的第三代也正在創造更多代表未來的創業故事。
“但浙商移民創業的質量仍值得探討,發展潛力不是很大。海外浙商總體發展水平不如國內浙商。”一名研究浙商的學者對本報記者表示,一方面受到能力限制,一方面也受移民國的產業環境和移民政策影響,很多行業移民不能進入,例如金融、電信、資源等。
在中國的外國創業者也有一些難邁的坎。
早些年在中國工作的時候,就有一個朋友提醒Rina,在中國,要非常靈活、隨大流。如今她更深刻地意識到,作為外國人在中國很難把產業做得很大,在中國一定需要一個很好的合作伙伴,而且關鍵的時候“關系”對一家公司也能產生很大的影響。
“中國的創業環境競爭非常激烈,作為一個外國人,不知曉中國的市場情況,而且消費者、技術、創新速度前所未有地在發展,所以必須吸收本土的東西,建立非常好的資源網絡。”Philippe說。
來自南美、在美國長大的Sebastian Martin則是這樣解讀“人脈網絡”:“國外的人們會覺得中國的‘關系’更多是送禮、吃飯,甚至和腐敗聯系在一起,但是在用美國,其實是通過關系產生影響。其實關系不僅對中國人適用,對外國人也適用,因為在外國我們也要建議人際關系的網絡,可以認識到不同的人,這對于我們創業非常重要。”
除了這些隱形的壁壘,有一些障礙顯得更直接。
Sebastian告訴本報記者,在香港設立公司一兩個禮拜進行審批后就能獲得營業執照,而在上海這個過程有可能會長達6個月。
“在中國創業,必須要有在線的服務,建立自己的網站,就必須要有一張互聯網內容提供商的許可證(ICP證)。要獲得這樣一張證書,有哪些規定,北、上、廣這三個城市的部門機構都會給你不同的答案。”Mark說。
Sebastian更直接地遭遇了“拆遷”之痛。他的咖啡館原本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房主突然告訴他們決定搬遷。“我毫無選擇,必須選擇其他場地,找一個類似的較好的場所來經營。”
 氵厥 水一橋爆破視頻回顧
氵厥 水一橋爆破視頻回顧
 首屆隨州旅游形象大使選拔賽15強名單出爐
首屆隨州旅游形象大使選拔賽15強名單出爐
 小伙夜間被捅多刀 幸遇武警戰士轉危為安
小伙夜間被捅多刀 幸遇武警戰士轉危為安
 先撞限高再撞橋 肇事司機轉頭跑
先撞限高再撞橋 肇事司機轉頭跑
 無牌摩托上街 一查竟是盜搶車
無牌摩托上街 一查竟是盜搶車
 集體財產遭破壞 村中“惡霸”誰來管?
集體財產遭破壞 村中“惡霸”誰來管?
 隨州市第二屆運動會青少年組跆拳道比賽舉行
隨州市第二屆運動會青少年組跆拳道比賽舉行
 隨州市城投公司改善市民居住環境
隨州市城投公司改善市民居住環境
 隨州市舉行“法律服務走近殘疾人”活動
隨州市舉行“法律服務走近殘疾人”活動
 隨州高考考生走出考場
隨州高考考生走出考場
 師生精心培育太空蔬菜品種
師生精心培育太空蔬菜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