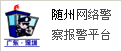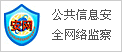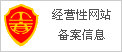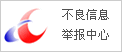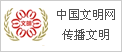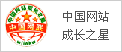方晉:中國迎來公益事業(yè)大發(fā)展
【方晉:中國迎來公益事業(yè)大發(fā)展】11月17日,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方晉在“第四屆中國公益論壇”上表示,不論是在全球,還是在中國,公益事業(yè)都進入了一個大發(fā)展的時期。這可能與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觀念的轉(zhuǎn)變和信息化、全球化有很大的關(guān)系。越來越多的個人,越來越多的企業(yè),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家,不管是出錢還是出力,投身到公益事業(yè)當中。同時,政府也在積極地鼓勵社會公益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迎來了公益事業(yè)大發(fā)展的趨勢。
11月17日,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方晉在“第四屆中國公益論壇”上表示,不論是在全球,還是在中國,公益事業(yè)都進入了一個大發(fā)展的時期。這可能與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觀念的轉(zhuǎn)變和信息化、全球化有很大的關(guān)系。越來越多的個人,越來越多的企業(yè),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家,不管是出錢還是出力,投身到公益事業(yè)當中。同時,政府也在積極地鼓勵社會公益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迎來了公益事業(yè)大發(fā)展的趨勢。
方晉表示,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國公益事業(yè)大發(fā)展,中國企業(yè)、中國企業(yè)家、中國的老百姓,對公益事業(yè)越來越關(guān)注,越來越投入,中國的公益組織會走出去,中國的資金、人才和技術(shù),也會走出去,和其他國家的公益組織一起合作,推動全球公益事業(yè)的發(fā)展。
他認為,雖然現(xiàn)在公益事業(yè)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有很多企業(yè)家捐助巨資推動公益事業(yè),但相對于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和挑戰(zhàn)而言,公益資源仍然是有限的,仍然是稀缺的,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了只憑激情投入公益事業(yè)的階段,要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能產(chǎn)生影響,能最大化效果的地方。
方晉:非常感謝主辦方的邀請,讓我來參加中國公益論壇。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是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發(fā)起設(shè)立的一個全國性的公募型基金會,我本人到基金會工作了將近四年時間,做了很多跟公益項目有關(guān)的研究和政策倡導(dǎo)工作。我個人觀察到一個很重要的趨勢,不論是在全球,還是在中國,我們的公益事業(yè)都進入了一個大發(fā)展的時期。這個可能和我們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的提高,觀念的轉(zhuǎn)變和前面講到的信息化、全球化有很大的關(guān)系。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個人,越來越多的企業(yè),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家,不管是出錢還是出力,投身到公益事業(yè)當中。不用說那些國內(nèi)國外知名的大企業(yè)家,就像在座的李總、袁總,本身在私營部門工作,但現(xiàn)在也拿出很多的精力投入公益事業(yè),同時,我們政府也在積極地鼓勵社會公益事業(yè)的發(fā)展,中國發(fā)展到這么個階段,迎來了公益事業(yè)大發(fā)展的趨勢,這對我們所有從事公益工作的人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另外,公益事業(yè)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發(fā)展是分不開的。一方面,有很多問題是一些全球性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努力解決。比如環(huán)境問題,特別是氣候變化問題。另一方面,有些問題雖然是局部性,本地性,但是有一些共性的問題,比如貧困問題,所有的國家都經(jīng)歷過貧困問題,其他一些國家在減貧脫貧方面的一些好的經(jīng)驗,完全是值得發(fā)展中國家學(xué)習(xí)和借鑒的。
中國的公益事業(yè)起步的比較晚,可以說在前期,我們的很多公益事業(yè)的資金、人才、理念、技術(shù)、模式,都是借鑒了發(fā)達國家公益組織、公益事業(yè)的一些先進的經(jīng)驗和做法。我們基金會開展的很多公益項目,也得到了國際組織和跨國企業(yè)的大力支持,受益匪淺。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國公益事業(yè)大發(fā)展,中國企業(yè)、中國企業(yè)家、中國的老百姓,對公益事業(yè)越來越關(guān)注,越來越投入,我們在很多公益項目當中,也有一些好的探索,中國的公益組織也會走出去,中國的資金、人才和技術(shù),也會走出去,和其他國家的公益組織一起合作,推動全球公益事業(yè)的發(fā)展,這是我觀察到的第二個趨勢。
第三,我感覺研究在推動公益事業(yè),推動公共政策的發(fā)展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剛才王振耀院長提到比爾蓋茨先生最近的一次到中國的訪問,我看了他的講話,他強調(diào)的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比爾蓋茨基金會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依據(jù)科學(xué)的證據(jù)來做出的。為什么研究、證據(jù)很重要呢?雖然現(xiàn)在公益事業(yè)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有很多企業(yè)家捐助巨資推動公益事業(yè),但相對于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和挑戰(zhàn)而言,公益資源仍然是有限的,仍然是稀缺的,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了只憑激情投入公益事業(yè)的階段,我們要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能產(chǎn)生影響,能最大化效果的地方,這樣投哪里?怎么投?怎么做?這個決定從哪兒來的呢?還是來自于我們的研究,來自于我們的數(shù)據(jù),來自于我們的證據(jù)。在座的幾位討論人,王院長是中國公益院院長,袁總是搞數(shù)據(jù)的,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主要的工作是做政策研究、政策倡導(dǎo)的,我旁邊的Agi VERES女士來自UNDP,也有很強的研究實力。他們的很多關(guān)于全球民生、社會、貧困問題的建議也都是來自于很強的研究實力的基礎(chǔ)來支撐的。我也感覺到,未來我們做公益要特別注重基礎(chǔ)性的研究,需要證據(jù)的支撐。我們做的公益項目,也需要對它的影響、它的效果進行評估,這可能是我們未來做公益的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氵厥 水一橋爆破視頻回顧
氵厥 水一橋爆破視頻回顧
 首屆隨州旅游形象大使選拔賽15強名單出爐
首屆隨州旅游形象大使選拔賽15強名單出爐
 小伙夜間被捅多刀 幸遇武警戰(zhàn)士轉(zhuǎn)危為安
小伙夜間被捅多刀 幸遇武警戰(zhàn)士轉(zhuǎn)危為安
 先撞限高再撞橋 肇事司機轉(zhuǎn)頭跑
先撞限高再撞橋 肇事司機轉(zhuǎn)頭跑
 無牌摩托上街 一查竟是盜搶車
無牌摩托上街 一查竟是盜搶車
 集體財產(chǎn)遭破壞 村中“惡霸”誰來管?
集體財產(chǎn)遭破壞 村中“惡霸”誰來管?
 隨州市第二屆運動會青少年組跆拳道比賽舉行
隨州市第二屆運動會青少年組跆拳道比賽舉行
 隨州市城投公司改善市民居住環(huán)境
隨州市城投公司改善市民居住環(huán)境
 隨州市舉行“法律服務(wù)走近殘疾人”活動
隨州市舉行“法律服務(wù)走近殘疾人”活動
 隨州高考考生走出考場
隨州高考考生走出考場
 師生精心培育太空蔬菜品種
師生精心培育太空蔬菜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