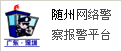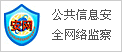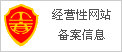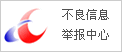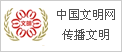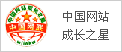全球資本流動亂花迷眼 中國怎么辦?
當前全球整體上正面臨資本過剩的困局,同時又面對著資本流動的變局。
一年多以前的2014年10月6日,德意志銀行外匯策略師George Saravelos曾預言,歐洲將面臨史上最大規模的資本流出危機:未來數年中,因全球經濟失衡,伴隨著歐元走弱,長端收益率下滑及全球收益率曲線平坦化,將看到歐元區歷史上最大的資本流出,歐洲資本將大量購買海外資產。今年12月1日,George Saravelos又發布報告稱,過去12個月中,歐元區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資本外逃(投資組合流動),其中固定收益凈流出達到創紀錄的5000億歐元。已經超出了經常賬戶盈余,造成基本差額赤字。
Saravelos表示,他的預期已經成為事實。中短期看,歐元區資本外流不可逆轉,未來數年,歐元區資本外流將會持續。大量歐洲資本(特別是德國)用于海外資產配置,而美國和亞洲投資者也正從歐洲撤資。另外,新興經濟體央行的量化緊縮政策加速了歐元區資本外流。不考慮歐央行12月份寬松政策的出臺,歐元的貶值趨勢顯然會持續下去。預期明年實現對美元平價,2017年跌到最低,預計兌美元0.85。此外,歐元對海外資本和債券的持續需求在未來數年會壓低全球債券收益率。
不過,美國紐約聯儲局官員反對Saravelos的觀點,認為歐元貶值是因為歐洲央行的刺激政策,而非資本外流導致。此外,歐元區始終保持貿易收支平衡,投資組合外流會被其他資本凈流入項目抵消,比如經常賬戶盈余,歐元匯率因此會保持穩定。
雖然不同機構對歐元貶值的原因有不同看法,但歐洲大量資本外流的現象不容否認。
資本外流的不僅是歐洲市場,在全球經濟危機積聚的大背景下,新興市場也是資本流出的重災區。有市場機構估計,在截至2015年7月底的13個月里,19個最大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凈流出總量達到9402億美元,近乎兩倍于2008-2009年金融危機時三個季度的4800億美元的凈流出總量。資本流出標志著一個急劇逆轉,在金融危機后的6年里,隨著新興市場幫助重振虛弱的全球經濟,它們曾得到強勁的資本流入。從2009年7月到2014年6月底,上述19個新興市場的資本凈流入總量達到2萬億美元。但現在情況開始逆轉,新興市場開始出現持續的資本外流。這種變化強化了一種擔憂:遭受經濟增長放緩和本幣走低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在交出它們扮演了多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火車頭的角色,轉而淪為需求的拖累。
中國的資本外流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十分醒目。根據中國官方統計,2014年上半年,不計對外直接投資(FDI),總計有260億美元資本流出中國。而根據美國財政部的估計,今年上半年該數字為2500億美元。7月份的數字估計為700億至800億美元。在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機制后,在8月份又流出了2000億美元。而根據彭博匯總的數據,2015年8月份估計有1416.6億美元資金流出中國,7月份的資金外流則達到1246.2億美元。中國外管局公布的數據顯示,1-9月,銀行累計結售匯逆差18827億元人民幣(等值3015億美元)。從這些數據看,中國面臨的資本外流壓力不小。
不過,在這一輪全球資本重新配置大潮中,中國不能始終扮演資本流出地的角色。美元和歐元區的逆向政策,推動歐洲成為全球儲蓄過剩、資本外流的中心,新興市場也受到較大的影響。但與歐洲和其他新興市場不同的是,中國存在扭轉局面,即從資本流出地變為資本流入地的可能。一是因為全球性的資本過剩和流動規模很大,流動性充裕;二是中國有規模巨大的內需市場,會在從投資轉向消費的過程中產生持續穩定的消費需求,這對于資本具有吸引力;三是中國經濟雖然存在下行壓力,但經濟增長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仍然保持較高速度;四是人民幣近期雖然相對于美元貶值,但相對于其他貨幣則保持升值態勢。
事實上,在全球資本移動的格局調整中,中國不能成為一個大的資本流出地,而應該調整政策,成為全球資本配置調整的一個承接者,中國有這種條件和可能性。
 氵厥 水一橋爆破視頻回顧
氵厥 水一橋爆破視頻回顧
 首屆隨州旅游形象大使選拔賽15強名單出爐
首屆隨州旅游形象大使選拔賽15強名單出爐
 小伙夜間被捅多刀 幸遇武警戰士轉危為安
小伙夜間被捅多刀 幸遇武警戰士轉危為安
 先撞限高再撞橋 肇事司機轉頭跑
先撞限高再撞橋 肇事司機轉頭跑
 無牌摩托上街 一查竟是盜搶車
無牌摩托上街 一查竟是盜搶車
 集體財產遭破壞 村中“惡霸”誰來管?
集體財產遭破壞 村中“惡霸”誰來管?
 隨州市第二屆運動會青少年組跆拳道比賽舉行
隨州市第二屆運動會青少年組跆拳道比賽舉行
 隨州市城投公司改善市民居住環境
隨州市城投公司改善市民居住環境
 隨州市舉行“法律服務走近殘疾人”活動
隨州市舉行“法律服務走近殘疾人”活動
 隨州高考考生走出考場
隨州高考考生走出考場
 師生精心培育太空蔬菜品種
師生精心培育太空蔬菜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