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打印機m7216—聯想7216的粉盒型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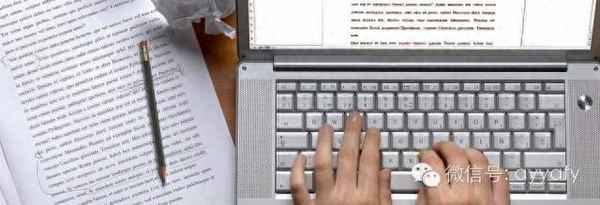
導語:青年翻譯家孫仲旭抑郁癥離世,在網絡上迅速蔓延,同行兔死狐悲,聯想到文化人的艱難處境和稿費制度。葉開表示,在悲痛之后,應該是對知識人價值評估的全面反思。改革開放30年有余,而對知識群體的整體評價依然是負面的、打擊的。在買車買房崇尚“土豪”的社會現實下,知識人是可悲可笑的新時代的“臭老九”。
稿費30年不變是一種奇跡,稿費征稅率太高是一種奇跡,800元起征點30年不變也是一個奇跡。這3個奇跡相加,抵消了30年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而如果不認真反思文化的價值,不給予知識分子合理的價值評估,導致缺乏文化原創力的強大驅動,那么建設文化強國的夢想就只能是南柯一夢。
我們的這個社會,在制度上,在認識上,對知識人價值的評價長期都是負面的,甚至是有意打擊的。從過去的貶稱“臭老九”,到“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迫害,無時不刻地提醒著知識的無用,知識分子的可悲與可笑。被制度性暴力和社會性暴力雙重迫害而斯文掃地的知識分子成為受盡嘲笑的可笑對象。他們唯唯諾諾、得患得失、優柔寡斷的蒼白面孔,和眼鏡片后躲躲閃閃的眼神,通過那時代電影人物形象的塑造傳遞到幾乎每一個觀眾的心中。至今很多人內心都保有對知識分子的發自內心的蔑視。
二十年前我隨女友去東北拜見泰山丈人時,被他們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嚇得一聲不敢吭。后來我努力表現,埋頭苦吃岳母制作的春餅卷大蔥,一下子吃了七個。太太后來說,岳父岳母當時沒有相中我,他們找太太嚴肅地說:他這么能吃,還是個舞文弄墨的,今后怎么養活你?現在聽起來像個笑話,當時卻對我形成了精確制導打擊。好在太太寬厚而機智,并沒有為此而遺棄我這沒用的家伙。
比我年紀小幾歲的孫仲旭,跟我是同時代人,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畢業,也面臨著各種人生的選擇,有些同學下海了,有些同學發財了,有些成官員了,都成了社會認可的成功人士。而孫仲旭為了自己的文學夢還在苦熬著。這種堅持的代價,在翻譯稿費普遍少得可憐的情況下,稍加渲染就會產生悲壯氣氛。有人計算過,一部15萬字的文學作品,認真的翻譯家需時3個月,按翻譯稿費千字60元計算,可得稿費9000元。根據現有的征稅稅率,減去800元起征額之后,剩下的8200征稅984元,翻譯家辛辛苦苦3個月所得僅為7216元,還比不上一名普通白領的月工資。如果沒有固定工作、固定工資收入,而專業從事文學翻譯工作,則這個文學夢代價巨大。據說孫仲旭曾把電腦里的400萬字譯稿打開給兒子看,說這是我的全部財產,今后你好好打理,可以回老家造間房子,討個媳婦。兒子說為什么不能在廣州買呢?孫仲旭說,在廣州連個衛生間都買不起!
作為中文系的正宗畢業生,又不幸一直熱愛著文學,我對這種悲慘的狀況是有切身體會的。20年前,我還是一名身無分文的大學畢業生,在上海地處偏遠的電機專科學校基礎部教語文,月工資176元,吃喝開銷后基本分文不剩。好在女友有條理,她頑強地攢著我們倆的零錢。20年過去了,我作為一名博士、一名老資格的編輯,工資漲到了每月2380元,因為通脹關系,這個月工資的購買力比20年前并沒有多少提升。在我的身上,看不到社會的進步,但這是我自己選擇的工作,我沒有什么怨言。90年代后期我們結婚時,太太學校分給她一間朝北的筒子樓,這種沒有廚、衛的宿舍間是當時最低門檻,擠進這里意味著你有個獨立空間了,等待你的將是漫長的苦熬。記得我們結婚那年夏天,兩人上午騎自行車去領了結婚證,中午樂呵呵地請同學好友吃了一桌飯,晚上死黨們又來我們房間鬧了一陣,大家都很快樂。熱鬧散盡,我們坐在一床嶄新花格子床單上仰望天花板,彼此微笑不言,幸福充滿心田,其實就是這么簡單。
幸福很短暫,那年秋天,貴為鐵路分局處座的丈人偕丈母娘南巡,來到我們的小窠,在我們戰戰兢兢的小心肝上,語重心長地說:“……萬里長征第一步,你們算是有個窩了。……你們得熬多少年才能混到一間像我們那樣的房子啊。”他們很友好,沒有責備,只有無邊的不屑和憐憫。他們離開后,太太淚水在眼眶里打轉。我們前不久發自內心的幸福,被這陣南巡的烈風吹干了。我們的幸福感本來好好地在我們身體里充溢著的,怎么突然就不見了?
在那個微妙時刻,很多同學下海了,去南方,懷著悲憤和熱望。我知道,他們的遭遇大多與我相似,簡單的愛情、微小的幸福,都經不起物質狂風的吹拂。一名大學畢業生,本應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本該享受簡單而無憂無慮的愉悅,最后都被逼下了大海。
二十年后再相聚,當年愛好文學的一幫死黨好多成了土豪、國企老總等,大家都白了頭,胖了身,人生各種滋味盡在不言中。現在大家回過頭來品咂人生,會看得更清楚:為什么我們要把幸福跟房子、跟金錢如此緊密掛鉤呢?為什么不能有更純粹的愛與快樂?如果社會不是形成了如此深刻的鄙視,如此制度性的貶抑,如果有基本的物質生活保障,我們平凡而愉悅地過一生有何不可?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成為百萬富翁的,也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在金融界、土豪界打拼。一個正常化社會,應該允許各種興趣的存在。而對于今天的稿費的高稅率,我們只是呼吁應該提高起征點到普通年收入的總額上,三十年前的800元起征點,現在應該提升到30000以上才合理。至于稿費稅率,更應該進行調整。這些,都是需要國家決策層關注的問題。看起來事小,但是在制度上的打擊,對一個國家文化生產力、原創力的壓制,是致命的。而缺乏文化原創力,只依靠山寨力,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是不明朗的,未來競爭會處于下風。除了制度性、社會性地對知識分子加以貶抑之外,有些出版社的無良做法,也加劇了這種悲壯感。
85歲高齡的大翻譯家王智量教授曾應某譯社之邀翻譯了俄蘇大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和曼德爾斯塔姆的一些詩,但他認真翻譯好交稿后,對方一直杳無音訊,也沒有任何人跟他說過稿子會何時出版。王智量教授是俄蘇文學研究大家,他過去曾為該社翻譯過一部《屠格涅夫散文詩》,前后發行超過百萬冊,這樣的暢銷書,出版社收益不可謂不豐厚,可是,大翻譯家王智量教授總共只拿到200元稿費!后來他反復追問,該社給他答復說,那個責任編輯早離開出版社了。聽王智量教授的傾訴,我很有些不滿,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新民晚報》上,呼吁尊重老翻譯家的勞動。文章出版后引起了一些反響,其他出版社托我致意王智量教授說有意出版王智量教授的所有譯作。我對出版社朋友說,王智量教授是離休干部,大教授,他本不是很在乎稿費的事情,但這事關出版社的自重和自律,也事關一個出版社對翻譯家勞動的基本尊重。我希望他們跟王智量教授簽合同時,對于公版書、暢銷書和常銷書,要簽版稅。后來,王智量教授把大部分的譯作,都轉交給了花城出版社的林宋瑜編審,因為林宋瑜編審對老翻譯家極其尊重,不僅親自上門拜訪,而且在翻譯家權益上做到了尊重,保護,盡力讓渡一些利益給譯者。
孫仲旭因憂郁癥而棄世,不一定跟翻譯稿費太低有直接聯系,但他以自己的決心,讓這個老問題再一次得到強烈的爆發。我內心里感到難過的同時,也認為無論如何都應該堅強地活下去,至少為了孩子。
葉開:原名廖增湖,1987年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2004年獲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現為《收獲》雜志編輯部主任、副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經發表和出版長篇小說五部,他對語文教材的研究與批判,引發了全國性的巨大影響,出版的專著《對抗語文》《這才是中國最好的語文書》《語文是什么》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書,葉開還被譽為莫言研究第一人。
本文轉自:愛英語愛翻譯






